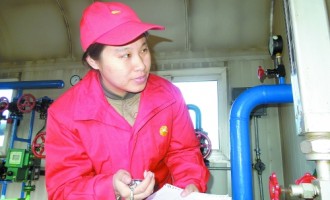一進入田洪軍的格子間辦公室,映入眼簾的是桌上厚厚的兩摞日記本。黃色卡紙打印的封皮,標注著日期,裝幀的整整齊齊。有的2本一裝訂,有的3本一裝訂。“原來都是一本一本的,隨著時間的延續,為了便于保存,我就簡單裝訂了一下。”
田洪軍1988年大學畢業,分配到齊魯石化勝利煉油廠電氣車間技術組,1992年5月調入機動處。從調入機動處踏入管理崗位那天,便開始了記日記的旅程,一天也沒落下,至今已經23年,目前記到第39本。“其實應該是40本,有一本在一次出差途中丟掉了,很可惜!”
拿起一本隨手一翻:1993年的3月7日,“美國主風機調試”;3月8日,第一次單試電機……3月12日,第二次開機,帶齒輪箱;13日,第3次帶負荷開機,手繪圖紙……17日,詳細記錄啟動時間的計算,從33秒到44秒再到45秒……“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晚上發生的事兒,就是在飯桌上我們還在討論主風機啟動時間和跳閘問題。”重新翻起這一部分日記,仿佛情景再現,立時勾起了田洪軍對當年的回憶。
那一年煉油廠一催化裝置擴容改造項目施工,3臺國產主風機需擴容更換為2臺美國進口的Roots主風機。田洪軍作為這一項目的負責人之一,白天跑現場,晚上整理資料。歷經14次開機試驗,田洪軍根據每次開機時系統電網的各項參數變化,修訂了“主風機開機操作規程”;最終于4月8日12:50,第15次開機正式運行。這本日記用整整一個月的時間,記錄了齊魯公司第一臺進口主風機的調試開機過程,成為歷史的見證者。這兩臺主風機一直運行了22年,直至今年一催化裝置拆除。
“那時電腦還不像現在這樣普及,每天的工作很多,就養成了記日記的習慣。”隨著工作崗位和工作重點的變化,日記內容也在變化。從開始的流水賬,到技術資料和參數的整合,再到技術管理和管理設想……有時只幾行字,發生事故時就會多記幾頁,詳細記錄事故時間、過程以及自己的事故分析。后來隨著電腦的普及,他將近年來發生的設備事故全部整理匯編存檔,隨時翻出來查看。自從2014年9月到運維中心后,每天的日記字數迅速增長,由原來的一兩頁到現在的3頁。
2015年9月,公司機電儀將進行專業化重組,因為有在生產廠從事電儀和大機組專業管理的豐富經驗,田洪軍奉命來到了運維中心運行調度科擔任科長。運調科不僅要負責日常生產和檢維修工作,還要負責全中心的檢維修計劃、投資計劃和各類生產費用管理,可謂是運維中心的“中樞神經”。過去在煉油廠只負責煉油廠的設備,現在要面對的是全公司的所有設備,“這個挑戰有難度。”來之前,他不是沒有考慮到。
他將自己在設備管理崗位上20多年來積累的“財富”毫無保留地拿出來,運用到新科室的建設發展中。在較短時間內,建立了近百個流程、十幾項制度。白天跑現場協調工作,等到下班環境安靜后,再開始看文件、寫匯報、匯總整理一天的工作,記日記。每天晚上基本上都是6點鐘之后離開辦公室。“我們田頭就是個工作狂人!”科員劉曉明說。
“每天不去現場,心里覺得空落落的。一到現場,看見那些設備,就會很充實,很滿足!” 田洪軍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:“現場設備有神靈”。
以前在生產廠時,他每天早飯后先給廠調打電話,詢問夜班設備報修情況,6點50準時出發去單位。途經煉油廠北區和南區時,他會先沿途查看幾個報修設備情況,掌握設備第一手資料,然后再回辦公室。這是田洪軍多年養成的工作習慣。來到運維中心后,他還是6:50出發,到班上后先去調度值班室“轉”一圈,先了解設備運行動態,電話與出現設備問題的生產廠設備管理人員交流相關信息,再回到辦公室。
走到調度科長這個崗位,面對如此多的設備和人員,現在的工作已經很難有一個上下班的時間概念了。也許深夜、也許凌晨,也許節假日,電話就是命令,就是沖鋒號,只要鈴聲響起,他總會第一時間趕往現場。拿一句運維中心機關人員的話說:“田科每天都充滿激情,從沒看到有疲倦的時候。”
對工作的過度投入,使得他對家人多了份愧疚。他清楚記得2014年12月26日這天,妻子生病住院,剛辦完住院手續,他就突然接到生產的求救電話,妻子說:“看你心神不寧的,快去現場吧!”情急之下,他找來岳父母,自己立即趕往二化設備搶修現場。后來妻子手術,也沒能及時趕過來,而是先由岳母代簽字和照顧妻子。今年8月12號晚上,妻子去上海看望孩子后坐火車返程回家,說好了晚上9點去接站,結果又因現場出現緊急情況要組織故障搶修,妻子只好獨自打車回了家……對于這些事兒,他也有自己的“招”,哄妻子說:“退休后我補償,陪你玩遍全國、周游世界!”
在他的日記本上,偶爾也會隨手摘錄幾句管理格言和感悟。“在設備維護上,我是個完美主義者。我相信通過管理的不斷強化、細化,一定可以達到事故零目標。”也許這便是田洪軍一直堅信并堅持下去的理由。(楊青青)